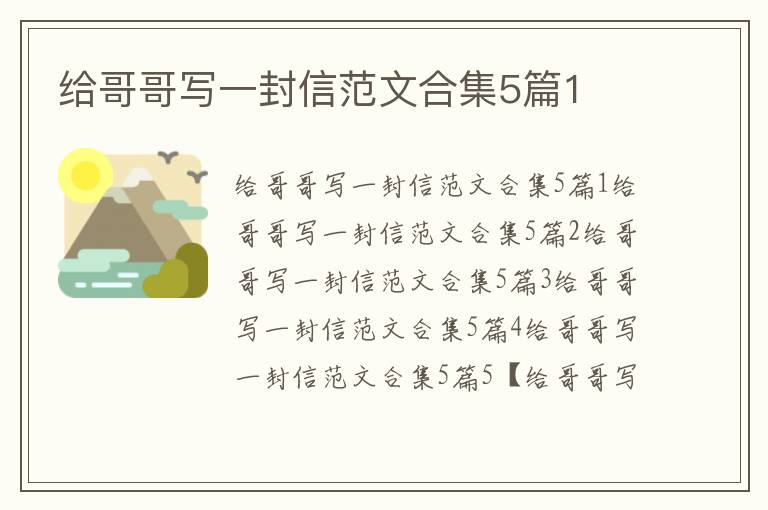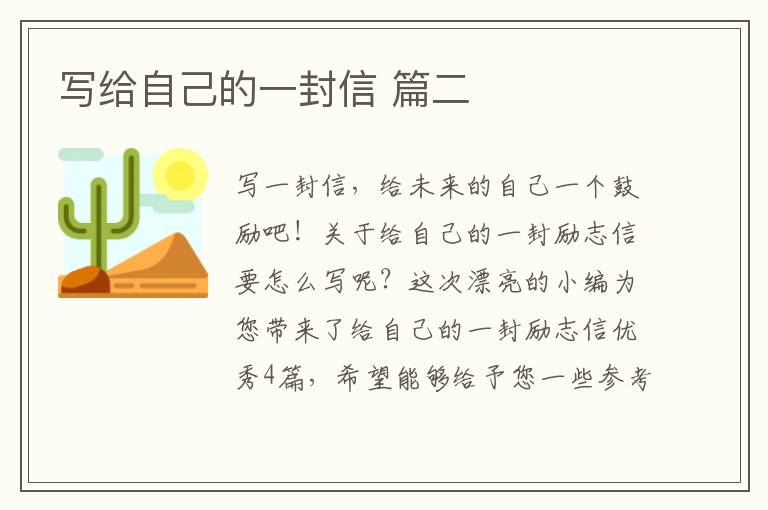亞坤夜讀丨見字如晤 (有聲)


“雙十一”我在網(wǎng)上買了一本小說《英國病人》。購書理由源于多年前看到的一張同名電影海報,海報上,黃沙漫漫,一個瘦削的中年男子將信紙放在自己腿上,手執(zhí)鋼筆正思索寫什么。
我不是頑固保守的人,卻非常喜歡寫信的畫面,也喜歡讀書信,其內(nèi)容或高談闊論,或傾訴心情,因為有一字一字的耐心鋪陳,總是讓人回味。
讀丘遲寫給陳伯之的勸降信,一句“暮春三月,江南草長。雜花生樹,群鶯亂飛”,便映襯出無盡的故國之思。人非草木,那叛變到沙塞之間的陳伯之因此決心重歸梁朝。建安時曹丕寫信給吳質(zhì),信中說,“觴酌流行,絲竹并奏,酒酣耳熱,仰而賦詩”,短短十六字,一個以文會友的盛世躍然紙上。而曹植寫給楊修的信則咄咄逼人:“蓋有南威之容,才可以論淑媛;有龍泉之利,乃可以論于斷割。”這是才高八斗的曹植,他說,才學(xué)要高過創(chuàng)作者,否則最好別開口。看來,作者與批評家的對立,自古有之。
我成長的年代與古代相去甚遠,卻對書信并不陌生。小學(xué)時常常聽收音機,廣播里某主持人說寫信給欄目組,被抽中了會有驚喜。為此,我在信紙上慢慢地寫下稍顯稚嫩的字,裝入挑選過的信封,貼上郵票,投入郵筒,等待郵差來取。本以為不會有回音的,因為這么多聽眾寫信,沒想到某天班主任竟當(dāng)著全班同學(xué)的面說,有北京給我寄來的信。信上內(nèi)容,早已被冗長的時光消磨,但初次收到回信后的喜悅感猶在。
最近的一次寫信則要倒推到11年前。那年,四川汶川遭遇了一場慘烈的地震。很多房屋倒塌,很多人被掩埋在地下,僥幸存活的人活在巨大的陰影之中。為了安慰他們受傷的心,校方要求所有高中生給災(zāi)區(qū)學(xué)生寫一封信。信上寫什么呢?提筆猶如千斤重,因為我只是一個旁觀者,寫的無非是堅強、振作、未來可期等字眼。我不知道我的信能否給予他們力量,只知道,當(dāng)我在桌前坐下,透過斟酌字句,透過筆在紙上摩挲,仿佛在與他們進行真誠的對話。而信件,可以捎去一個少年最虔誠的祈禱與祝福。
十余年一晃而逝,伴隨QQ、郵件、微信、電腦的興起,書信也慢慢地從生活中消失了。快節(jié)奏生活,讓一切行為都變得簡略、倉促。我們失卻了寫信、等信、回信的熱情。所以木心才說:“從前的日色變得慢,車、馬、郵件都慢。”
然而,從前終究是從前了。我們或可想象,像寫信等事件,在抹去時間的灰塵之后,會變成現(xiàn)世的美麗風(fēng)景。